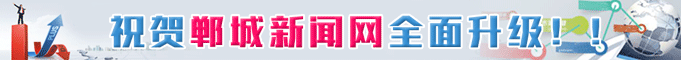——关于当下的小说语言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说书:小说语言的基因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王安忆的物质指的是从日常出发、终究又要回归到日常的世俗性,这样的物质与精神并无高下之分,淤泥里会开出莲花,而凭空绘出的莲花却只是镜花水月而已,等不到一场真实的枯萎。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 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它可以唯美,因为唯美也是万千世态之一种,但自拘于耽美却会导致迅速的干涸,就像废名的《桥》难有一个收梢,它再美些,也只是一个梦,甚至是在梦一个梦。小说语言可以准确,一枪击中一个目标,因为所指毕竟是能指的磁石,完全摆脱所指的能指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也可以言不及义、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现实里的语言有多少是直奔靶心而去的呢,我们的“说”更多时候只是一个个“消逝的中介”,指引,然后消逝,从来不驻留,就像莫言的“耗费”的写作。 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明乎此,写小说的人就应该领会,动笔之初,自己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属己的叙述声音。 余华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好比一个人刚从子宫里出来,要是脑袋挤扁了,这个人就不会聪明。”余华对于“第一句话”的推敲就如同歌唱家的试声,他们都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调”。不过,叙述声音的合适与否实在微妙,以至于太多小说家都在感慨,开头是难的。其实,万事开头难,头开好了,一切也就顺畅了。比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这样开头的:“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就是老马,老马背地里说起朋友,却一次也没有提及老杨,外人不知底细,都以为他们是好朋友。”这个开头一下子确立了一个在是不是朋友、当不当朋友之类的世情泥淖中迷失却又徒劳地想一一厘清的倔强的叙述声音,有了这样的叙述声音,刘震云那个既无奈又激越的喟叹也就呼之欲出了:到哪里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真言? 误区:强作典雅与一味诚恳 从以上体悟出发,我认为当下小说的语言相应地存在两点问题。 第一,小说语言强作典雅,好像用典雅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就一定是高级的小说似的,殊不知雅也许只是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俗有时候反而是泼辣的,一鞭子就是一道血痕,更何况小说原本只有好坏之分,哪有高级、低级之别。可以举一组经典作家的比喻略作对比:同样是形容一张抹过官粉的丑脸、黑脸或是老脸,老舍说虎妞的脸仿佛“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赵树理说三仙姑的脸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可惜的是,驴粪蛋一类的词汇入不了很多小说家的法眼,他们恨不得找出所有带“玉”字偏旁或是其他其来有自、一打眼就极高贵、雅训的词汇来砌成自己的小说。比如,葛亮的《北鸢》说姐姐昭德虽是病容,仍是“刚毅朗净”的样子。“刚毅朗净”一词美则美矣,跟样子却不太搭,更不必说我想象不出“刚毅朗净”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样子,昭德于我始终是模糊的。小湘琴被枪杀,一向冷清的房间围满了看客,葛亮说,“大约从未这样充盈过”。“充盈”一词灵性十足,但我无法把它和一个人头攒动的凶杀现场联系起来,我还是觉得,像“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一类的描述要带劲许多。再如,叶弥《香炉山》说一弯弦月“清丽淡雅”,散发出“蕙心兰质”,说花雕的味道“纯正雅致”,汪曾祺要是看到这些典雅到不知所云的词汇,一定会哑然失笑的:“什么叫‘绚丽’?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绚丽’嘛。” 第二,小说家们只是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就像不太高明的歌者只会用自己的真嗓子嘶吼,他们还不懂得运用“假声”“花腔”,不明白在自己和演唱之间应该隔着一个由自己发出却又不是他自己的腔调——这里的腔调,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就是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的合适的叙述声音。忽视对叙述声音的寻找和淬炼,起码给当下小说写作带来如下后果。 首先,就好比看戏、听歌,我们要听的可能并不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戏文和旋律,而是名角、巨星各有各“味”的唱,读小说时,我们要看的就不只是小说家说了些什么,更是他们各有各“味”的说本身,我们有时还没等弄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就已经被有意味的说裹挟而去。遗憾的是,当下某些小说家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吊”出属于自己的嗓子,他们的写作当然就是面目雷同的,哪有辨识度可言,他们要想出彩的话,就只能乞灵于说的内容,说直白一些,就是借题材的光——底层写作、民族秘史,不一而足。 其次,真嗓子的音域是狭窄的,只能在有限的音区内徘徊,同理,不为每一篇小说打造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而是统统由小说家本人赤膊上阵,他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音域内发声,他所有的创作好像是孪生的,写一篇与写一百篇没有本质的区别,像一团既相互游离又彼此交融的云彩,没办法清清爽爽地择出其中的一片来,哪像一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知道是《狂人日记》,再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就知道是《故乡》——我想,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文体家”,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为每一篇小说确立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声音既殊,文体必异。 作者简介 翟业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0日 24 版) |